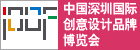每个对文明和博物馆有所了解的人都会知道,主宰世界的西方文明的背后是博物馆,为这些博物馆提供展品的真正收藏家们在收集他们的第一件藏品时,多数时候根本不会想到他们所做的事情将会有怎样的一个结果。这些真正的第一批收藏家,在他们得到的后来被展出、分类做目录的(第一批目录就好比第一套百科全书)那些大藏品的第一件物品时,多数时候甚至根本没发现它们的价值。——摘自奥尔罕·帕慕克《纯真博物馆》
正如现在的每一次旅行,我再次来到伊斯坦布尔的原因确实是与“博物馆”有关。在这里,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和美术馆的馆长和策展人们齐集,在一个原奥斯曼帝国银行总部的奢华建筑中举行三天的会议,对“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艺术收藏和展览相关的哲学、道德及实践议题进行讨论”。在嘉宾发言、咖啡小憩、饭后社交的间隙,我不禁自嘲地想这个会议与其叫“超越危机的美术馆”,不如大胆一点叫“博物馆如何拯救世界?” 这种英雄式的、盲目的使命感,跟小说《纯真博物馆》中帕慕克笔下的凯末尔对芙颂的迷恋如出一辙,甘愿为称之为“爱”的不可描述之物从其所属的外部世界中退出,向内部的执迷崩塌。
从一个实用主义的角度看,博物馆确实是我去过和即将要去的每一个城市的坐标,那些google地图上的小红点,往往是我对一个城市的记忆和想象;如果一个地方缺少博物馆,我就会用小说来填充,阅读当中的那些畅快无比或不堪忍受的片段,一旦与某种曾经有过的视觉记忆相结合,就可以放大或强化不曾拥有过的经验:例如在《2666》最长的章节“罪行”当中,你身陷那些没完没了地被谋杀的墨西哥女工和她们无法被记住的名字,失去了理解作者意图的耐心,此时,从某个展览的录像作品中看过的墨西哥边境小城漫山遍野的废弃汽车的场景,就会在一瞬间混杂着血腥的尘土气息扑面而来。这大概是虚构/想象(fiction)与博物馆可能建立的第一层关系:对经验和感知的无尽欲望。
如果说城市的历史往往被保存在博物馆当中,它们代表的往往是一种无人称的官方记忆。从这层意义上说,一个城市有帕慕克这样的作者是幸运的。他不仅在其自传性著作《伊斯坦布尔》中直呼其名,在《我的名字叫红》中用一个悬念故事的载体细致地书写土耳其细密画的传统,更将《新人生》中已经显露出来的,用貌似微不足道的日常物品书写土耳其历史的执着在《纯真博物馆》中发扬光大。由于当代艺术及其臭名昭著的概念,我们已经不再为貌似毫无审美价值的日常用品以大规模的姿态进驻博物馆的事实感到惊讶,它们大多数带着某种使命而来,却并非它们本身。在帕慕克的纯真博物馆里,我们不会看到杜尚式的大胆宣言,他是真心要为物品立传,在他的精心陈列下,这些物品就像个恋人一样絮絮低语,唯一的问题是,经年日久,这种低语也可能成了忆苦思甜式的牢骚。在去往纯真博物馆之前的晚上,我们在市中心一家有土耳其传统民间音乐演奏的餐厅预订了位置,邻桌的二三十个年轻人似乎正在为一位女孩庆祝生日。餐厅的价格与一般餐厅比起来偏高,但餐单的选择之少却有点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邻桌的年轻人到此似乎完全不是为食物而来,我在欣赏音乐之余只见他们不断地添加雷基酒,兴之所至,便随着音乐和酒意随心起舞。雷基酒闻起来有股浓烈的茴香味,喝的时候往往要兑水或加冰,这种原本透明、兑水之后变成白色的液体对土耳其人来说似乎有着神奇的魔力。凯末尔在小说中后部分就几乎到了手不离酒的地步,有趣的是帕慕克也没有把他当做一个酒精中毒者来写(在西方小说,尤其是畅销书当中,创伤化的主角往往就被刻画为酒精中毒者,对戒酒的描写就是主角自愿或非自愿的身心康复过程);而在博物馆里,展柜中更是隔三差五地就正儿八经地陈列着一杯雷基酒,据说雷基酒的后劲很足,“是爱神为恋人所调制的,只有真心为对方付出,一心想着所爱的人才能品尝出它所隐藏的凄美底蕴。”1
事实上,不停地喝着雷基酒的凯末尔在《纯真博物馆》中简直是过分清醒,他以编年史一样的、全知全能的古典口吻叙述着自己和芙颂的故事,像无数个全景摄像头一样无时无刻、巨细无遗地记录下芙颂的一举一动及其周遭的一切,甚至到了干扰读者想象力和阅读乐趣的地步。尽管帕慕克部分牺牲掉了这个人物的可信性和亲和力,却为20世纪70年代土耳其世俗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绘制了一幅极其生动的画卷:从土耳其到刚刚崛起的本土电影工业,到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以文化西化和消费主义为代表的现代化进程,再到土耳其内战及保守派隐约的历史背景,无不被这些摄像头揽入镜中。帕慕克为小说的每一个章节都精心布置了一个展柜,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文本叙事和视觉叙事之间的差异之处,对于一些相对纪实性的章节,比如“一些讨厌的人类学事实”这一章,文本谈到的是那一时期土耳其报纸上刊登失去贞操的未婚女孩们被黑条蒙住双眼的照片的保守习俗,展柜当中就只要展出收集而来的报纸页面便已经能呈现足够的关联;而另一些比较情绪化和抽象的章节,例如“秋愁”中讲述凯末尔与未婚妻栖居海边雅丽多月却完全无望摆脱对芙颂的思念和愁绪,这也是凯末尔越发转向内心执迷的转折点,展柜的陈列就犹如一幅立体的超现实主义油画,那种绵长而又强烈的绝望被凝结在博斯普鲁斯海峡黑色的海面上。
相关新闻
- [艺术关注]茅台雅韵•保成丹青 | 宁保成书画(08-17)
- [艺术关注]展览预告 | 生生流转——安徽大学(06-21)
- [艺术关注]风鹏正举——吉安市青年画家十人作品(04-13)
- [艺术关注]著名画家魏兴无参加将军部长书画研讨(11-23)
- [艺术关注]第十四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版画作品展(07-06)